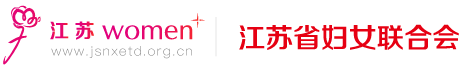老家的凌霄花,是母亲的心头好。每到夏天,那藤蔓便攀着院墙,一路向上,开出许多橙红的花来。花朵形如喇叭,颜色鲜艳,在绿叶的衬托下,格外醒目。母亲常说,这花好看,还能入药。
我幼时不解花事,只觉得那花爬得高,开得热闹,便也欢喜。后来年岁渐长,才晓得母亲爱这花,是有缘由的。
母亲栽的那株凌霄,就长在院子的东南角。起初不过是一截枯藤似的枝干插在土里,母亲日日浇水,竟也活了。第一年,只抽出几根细藤,攀着墙缝,艰难地向上爬;到了第二年,藤蔓便粗壮了些,叶子也茂密了起来;第三年竟次第开出了花。母亲见了,脸上显出少有的笑容来。
凌霄花开时,母亲总要摘些下来,晒干了收着,她说这花能活血化瘀,治跌打损伤最好。村里人有个小伤小痛,常来讨要,母亲从不吝啬,有时还亲自煎了药送去。我那时不解,问母亲为何这般费心。母亲只道:“乡里乡亲的,帮衬着些,是应当的。”
母亲的话,我一直深信不疑。只是后来到城里读书,见了些世面,便觉得母亲太过老实,容易吃亏。有一年暑假回家,正赶上村里的王婶来讨凌霄花。王婶的儿子摔伤了腿,要这花入药。母亲二话不说,便摘了一大把给她。我见了不免嘀咕:“就这么白给了人?给的也太多了吧。”母亲却道:“花开了就是要用的,藏着做什么?”我那时年轻气盛,只觉得母亲太过善良。现在想来,倒是我浅薄了。
母亲不但将花送人,还常常将晒干的凌霄花寄给我。我在城里工作,每每收到这些花,便想起老家院子里那一片橙红。有一回,同事见了,问我这是什么,我答是凌霄花,母亲寄来的。同事笑道:“你母亲倒是有心,这么远还寄花来。”我听了,心里忽然一热。
母亲寄来的花,我大多泡了茶喝。那茶色橙黄,味道微苦,喝下去却觉得浑身舒坦,确有舒筋活血的功效。母亲不识字,却懂得很多生活的窍门和道理。
前几天,我回老家看望母亲,经年不见,盛开的凌霄花让我叹为观止。那些橙红的花朵从青砖墙头、灰瓦檐角倾泻而下,像一匹被风掀开的锦缎,又似凝固的晚霞突然有了生命。每一朵花都昂着脖颈,五瓣绸缎般的花瓣向外翻卷,露出内里蜜糖色的脉络,花蕊如金丝般颤动。阳光穿过半透明的花瓣时,会在地面投下琥珀色的光斑,与攀缘的藤蔓影子交织成流动的壁画。
刚下过一场小雨,水珠顺着藤蔓滴落,整面花墙便有了泠泠的声响。老墙的斑驳、新叶的翠碧与花朵的灼艳层层叠叠,连空气都染上了甜腥的芬芳——那是阳光烘焙花蜜的气息,混着砖缝里青苔的潮湿,酿成令人微醺的夏之味道。偶尔有雀鸟掠过,惊起几片凋落的花瓣,那飘摇的弧度恰似火焰熄灭前最后的舞蹈。
母亲正在摘花,见我回来,忙放下手中的活计。我注意到,母亲的手上生了些老人斑,动作也不如从前利索了。“今年的花开得好。”母亲说着,递给我一朵刚摘下的凌霄花。我接过花,发现花瓣上还带着水滴,湿漉漉的。忽然想起小时候,母亲也是这样,常常摘了花给我玩。那时的母亲,手上还没有这些斑点,动作也轻快得多。
“还寄那么多花给我做什么,城里都有卖的。”我忍不住说道。
母亲笑了笑:“城里卖的哪有自家种的好。再说,寄花给你,就当是寄个念想。”我听了,一时语塞。原来母亲寄花,不只是为了它的药效。
晚饭后,我和母亲坐在院子里乘凉。月光下,凌霄花的轮廓显得格外柔和。母亲忽然说起我小时候的事,说我如何顽皮,如何不爱吃药,只有在药汤里加上几片凌霄花的花瓣,让药汤显得漂亮些,我才肯喝。这些事我几乎都记不清了,母亲却说得真切,仿佛就在昨日。
“人老了,就爱想从前的事。”母亲叹道。
我望着月光下的母亲,发现她的白发比去年又多了些。那株凌霄花在夜风中轻轻摇曳,发出细微的沙沙声。我突然明白,母亲爱这花,更因为它见证了我们母子的岁月。
回城前,母亲又包了一大包晒干的凌霄花给我。我没有推辞,小心地收进了行李。我知道,这包花的重量,远不只它本身的分量。
如今,每年的初夏时节,我的书桌上常摆着一小瓶凌霄花。工作累了,看上一眼,便仿佛看见老家院子里那片橙红,看见母亲在花下忙碌的身影。有时深夜伏案,恍惚间似乎闻到那淡淡的花香,便觉得母亲就在身旁。
世间的爱,有许多种。母亲的爱,就像这凌霄花,不张扬,却执着地向上生长;不艳丽,却温暖了岁月。它攀附在记忆的墙上,一年又一年,开出新的花朵来。花开花落,岁月更迭。唯有那橙红的花朵,叠在心头,永不褪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