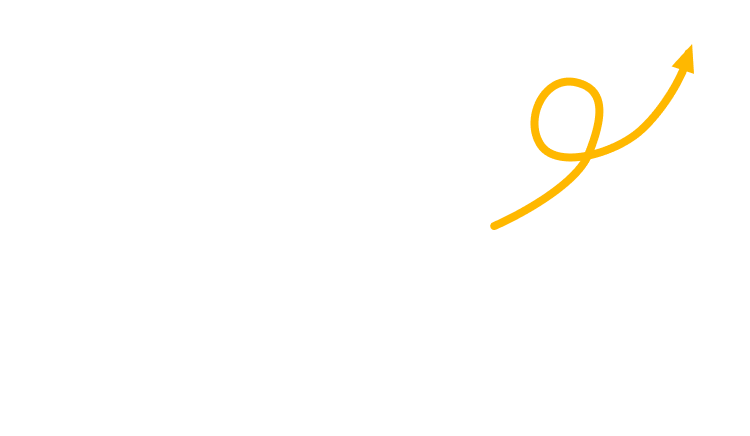先生,我不敢多停留
文 高桂荇
严冬,天阴阴的,寒气如冰,好像要下雪。
从北京王府井大街向西,是灯市口。往西走两百米光景,便是丰富胡同。朝里望,胡同窄窄的、弯弯的,看不见底。
胡同有历史。乾隆时,称风筝胡同,居民大多做风筝;宣统年间,叫丰盛胡同;新中国成立后,改为丰富胡同。胡同19号,曾住着老舍先生。
按箭头所指,我们踏步胡同,从东门进。跨槛入门,玲珑有致的一块影壁映入眼帘,中央镶嵌一个“福”字,有王羲之的味道,落款是先生的夫人胡絜青。转身进院,又是一座影壁,还像刚才的模样,如出一辙。
时间为经,地点为纬,先生的生命波澜起伏。若论中国近现代史,说先生是一道缩影,不为过。咿呀学语时,清政府风雨飘摇,“满城都是刀光血影”,先生深感弱国的悲哀。英伦时光,先生对异邦文化兼容并蓄,探索国民性,寻求强国之道。抗日战争爆发,男儿请缨,先生化笔为枪,投身宣传第一线。赴美交流,先生心系国家,北京土地的哺育、滋养,杂院里的老少街坊,在先生笔下鲜活生动。“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”,乃肺腑之语也。新中国焕然站立,先生疾疾归国,义无反顾。
耸立眼前的,是两棵树,比屋脊还高许多。铁干竖直,黛枝遒劲,蓬蓬然如一对巨大的伞骨。抚摸,端详,我发现是柿树。哦,那年春天,先生和夫人亲手栽种。俟秋,红柿满枝。天日地月,夫人美其名曰:“丹柿小院。”好景随春,好运顺秋,其时,先生的生活颇是随心。早起练拳,上午写作,下午办公。长河星空,相约清澈,其文字深刻、伟岸。闲暇之际,养花,逗猫,玩牌。岁岁年年,院内总是鲜花绚丽,尤以冬菊为著,熠熠照人。这样的时光,地利,人和,心安。我站在树下,仿佛看到红柿满挂在头顶,芬芳缭绕。而先生一家,则其乐融融矣。
文学巨匠,浩如繁星;喜怒哀乐,不一而足。上大学的时候,老师讲现代文学,我就知道,1966年8月24日,是个悲哀的日子。那一天清晨,年近古稀的先生独自走出小院,踯躅,彷徨,一步一回头。京城西北角,有个太平湖。然而,太平湖里不太平,先生凄然行吟。世道不无荒唐,先生的心事何人得知?天黑下来了,京城灯光迷离。冷月俯望,心怀几伤?先生坐了一夜,起立,回眸,纵身投湖……人间的故事,都逃不过分离。但是,先生这样的诀别,太无奈,也太潦草了,让人几度扼腕。暌隔四十年,远处八宝山墓墙上刻着先生自己的一句话。文字是安静的,却又振聋发聩。先生曾说:“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,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与小凳之间,笔是枪,把热血洒在纸上。可以自傲的地方,只是我的勤苦……在我入墓的那一天,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,上刻:文艺界尽责的小卒,睡在这里。”我就想,煌煌在天的先生可否如愿?
院子西南角,端坐一口大缸,面径一米有余。外壁两字:鱼缸。先生喜欢养金鱼。繁大的创作,间以小歇,与鱼同乐。年复一年,雅兴盎然。而今,酱黄色大缸犹在,却空空如也,水和鱼呢?是的,人去了,鱼没了,剩下孤零零的大缸,披霜凝雪。“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?”古之人不余欺也。
世相纷纭,水落而石出。如今,先生的故居已成展室。盘桓院中,我百思汹涌,我不想匆匆地去参观。先生执笔著文,数千万言。然而,先生从不自满,精益求精。难怪有人啧啧仰止:“世态画卷看茶馆,龙须沟畔换新颜。骆驼祥子苦挣扎,四世同堂皆京味。”我回忆先生的绮丽文章,却是这样的定语:作品高山兮耸然立峰,生命一湖兮惨烈落底。
一字,一树,一缸,有生命的,没有生命的,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。万丈红尘,生如烈焰,文人的命运可有谶语?曾几何时,敞口大缸里的金鱼是快乐的,红悠悠自由自在。柿树年年红,彤彤的水灵甜美。影壁的福字,是红火火的胜庆。正反两面都是福字,两个影壁,事事如意。哦,年年有鱼(余),事事(柿柿)如意,壁壁(比比)得福。但愿先生的生命璀璨不朽,驭仙风、驾祥云,微笑向暖处,锦笔再生花。
我徘徊于小院里,转了三圈,遐想先生的一帧帧生活场景。来参观的络绎不绝,大多是年轻人,还有小学生。我观摩了三个展室,浮光掠影。正房中堂的地方,有先生一张照片,眼神深邃、忧戚、仁厚。前足沉重,后脚寂寥,我不忍细看、不敢深思。眼底霜浓,心底雪重,念予眉间,谁人来评?我离开院子,再也不敢停留,怕自己悲楚。好像一停留,历史的白发就会飞到我头上。
临走,殇云漫天。时近黄昏,天空却比我们来时亮了。冷还是冷,可感觉比来时轻缓了些。天地大情,故居沉沉淹没在暮霭中。望穿天涯,先生在哪里?我没能从先生的眼光里走出来。
回头,不走人行道了,太滞涩。跨步街道边沿,我往前大步走,口中念念有词:先生永在!
 分享
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