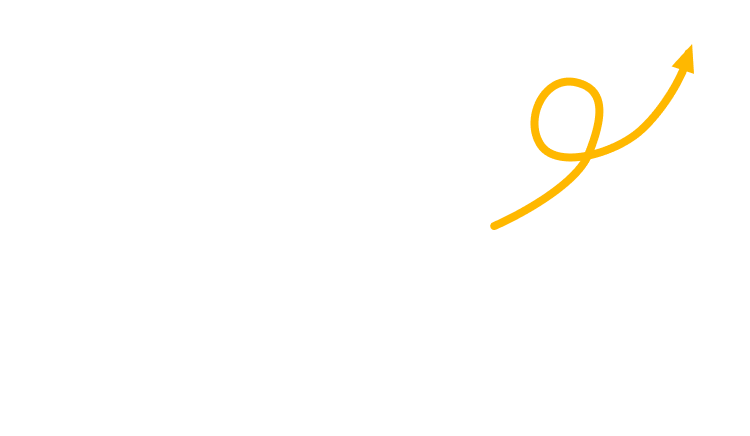吾乡青年恋人中有一习俗,女子常呼中意的情郎为木瓜,即傻瓜。男孩子并不懊恼,往往喜上眉梢。此间情意,渴望中仍见矜持,热烈里亦有含蓄,很有些《诗经》的风雅,让我想起《卫风·木瓜》:“投我以木瓜,报之以琼琚。匪报也,永以为好也! 投我以木桃,报之以琼瑶。匪报也,永以为好也! 投我以木李,报之以琼玖。匪报也,永以为好也!”关于这首诗的主题,历来有许多分歧,其中成于汉代的《毛诗序》中“外交感恩诗说”的影响极大:“木瓜,美齐桓公也。卫国有狄人之败,出处于漕,齐桓公救而封之,遗之车马器物焉。卫人思之,欲厚报之,而作是诗也。” 此说得到很多学者的支持,重要代表在宋代有严粲(《诗缉》),在清代有魏源(《诗古微》)。与“外交感恩诗说”几乎同时的“臣下思报礼说”,亦有一定的影响。这类解读有一定依据,加之政治因素,遂成正统,不可撼动。
有趣的是,到宋代,一向主张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的朱熹却提出了“男女相互赠答说”。他在《诗集传》对前人的观点加以质疑:“言人有赠我以微物,我当报之以重宝,而犹未足以为报也,但欲其长以为好而不忘耳。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,如静女之类。”这一看法得到后世学者的普遍认同。
剔除纷繁复杂的政治因素,让这首诗回归到爱情层面,也许诗味更浓。金启华先生译注的《诗经全译》明确加注:男女相互赠答,情深意长!
这首诗有些特别,没有展开环境描写,不像《关雎》《蒹葭》《野有蔓草》等篇,主人公的活动舞台美得让人心旷神怡,使人心荡神驰。《木瓜》篇没有舞台,或者说,他们相遇的地方就是舞台,无须设计舞台,只要给他们一个空间,华美的爱情就是天地间最美的诗剧。爱情一旦擦出火花,它的光芒一定让周遭的一切黯然无光,无须再用山水来陪衬,也不必再用花草来渲染。甚至不用语言,不用眼神,只一个动作,就是默契。
你看,那个女孩“投我以木瓜”。动作是“投”,很多学者将“投”字理解为“赠送”,固然有道理,但太现代化,须知,那是一个去古未远的时代,投字也应多少保持它的本义:从手,从殳(古兵器),合起来表示手拿兵器投掷。所以投的本义是投掷,说文解字明确指出:投,擿(掷)也。只不过,这里投的施动者是女子,兵器变成木瓜、木桃、木李,是果实,不但不具攻击性,反而有一种美感。如果要说有攻击性的话,那也是美的攻击,攻击的目的不是要取对方性命,而是要俘获对方的心。一个果实,何以有如此巨大的魔力?《诗经》的时代,男女分工明确,男狩猎,女采集。《国风·召南·野有死麕》篇中“有女怀春,吉士诱之”,吉士就是没有结婚的美男子,当他打死一只麕时,迫不及待地用白茅裹好,送给他日思夜想的美丽女子。同样,当女子采集到木瓜时,也是骄傲得很,顺手将一只小巧的木瓜扔了过去,他轻舒修长的臂膀,接瓜在手,然后满怀喜悦地把自己的佩玉解下,也轻轻地抛给女孩,今天还没有去打猎,先将这块美玉送给你。然后彼此会心一笑。这是狩猎与采集时代特有的承诺,也是直接而富有诗意的表达。
人类的情感最早的传递方式一定是动作,语言是后来才产生的。这首几千年前的诗,居然就靠一“投”一“报”两个动作支撑起来,获得长久生命力,传唱不衰。掷果盈车的典故里也有“投掷”的动作:“安仁至美,每行,老妪以果掷之满车。”不过潘安大概是不会向那些老妇人报以美玉的。很多读者都认为以美玉换木瓜,男孩子有点吃亏。怎么说呢,只有我们现代人才会这样计较,诗中的男子可不这样想,“匪报也,永以为好也!”一块玉哪能报答投瓜之情?那可是女孩子欲以一生相托啊!一篇之中,反复吟唱,可谓三致意焉!款款深情,在男孩子看来,木瓜、木桃、木李已成了定情之物,就像后来的红豆,胜琼琚、琼瑶、琼玖多矣!唉,实在难以报答你的情意,怎么办呢?永以为好吧!是决心,更是承诺。
所以,如果有人送你木瓜,你一定要好好地爱她。顺便说一下,这里的木瓜是蔷薇科植物贴梗海棠的果实,多在夏秋二季绿黄时采收,也叫宣木瓜,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有载,并非我们平常吃的南方水果番木瓜,估计《诗经》时代的女孩还没见过这种果实,更别说采来送人了!
 分享
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