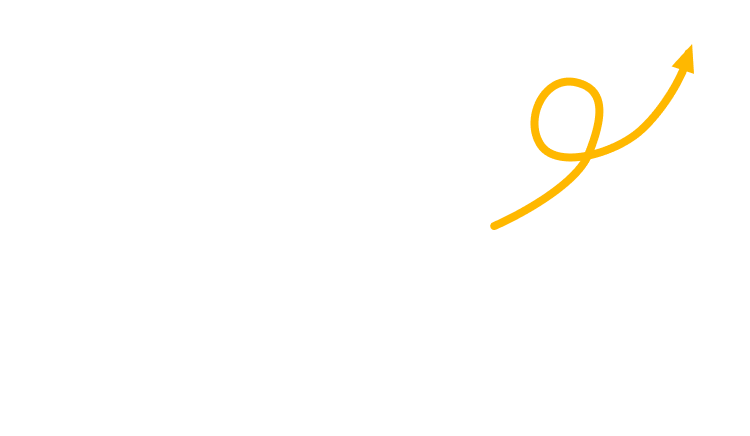1
从前的夏夜,咸涩的海风穿过植满美人蕉的院子,奶奶的蒲扇摇呀摇,摇出几个老掉牙的故事。奶奶不识字,故事是她从戏文里听来的,关于落难书生与狐仙,关于忠臣与奸佞,她翻来覆去地讲,直到每一个故事我都能原原本本复述出来。奶奶说,等我上学识字了,就能知晓更多千奇百怪的故事,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。我窝在竹椅里,望着满天繁星,心里萌生出一种奇异的渴望。
多年后回想,奶奶算得上我最早的文学启蒙者,正是那份奇异的渴望引领我走进了书的海洋。
我出生于东海边上的一个悬水小岛,小岛四面环海,无着无落,交通相当不便利,就像一块被造物主遗弃的土地。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,小岛还相对闭塞,岛民的生活如那半日潮,日涨日落,夜涨夜落,规律、单调,精神生活甚为匮乏。在岛上,书籍不是多数人的必需品,遂不常见,我像只饥饿的小兽,四处搜寻带“字”的东西,小人书,小姨的语文课本,邻居的旧杂志,甚至别人家糊墙的报纸。那种对文字的渴求,如同干裂的土地渴盼雨水。
至今记得那本小人书,插画里的爷爷穿咖啡色上衣,胡子花白,插画下的几行字我可以认出一半,加上拼拼凑凑猜猜,看懂了大致意思:爷爷为了送出紧急情报,倒在敌人的枪下,他握着孙子的手完成嘱托后,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我的眼泪簌簌往下掉,滴在书页上。文字的力量第一次击中了我——它能让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为之流泪,能让遥远的故事在我心里生根发芽。
上了学,尤其上了初中,阅读的机会多了起来,学校阅览室可以借书,岛上也渐次出现了租书屋,里面的书以言情、武侠类为主。有一回,我在岛上的文化中心挖到了“宝藏”,它们被装在墙角的纸箱里,管理员说,那是些没人看的书,所以搁置了起来。我小心地掸落书上的灰尘,每一本书都完好无损,甚至还挺新的——《雾都孤儿》《巴黎圣母院》《悲惨世界》《傲慢与偏见》……管理员见我喜欢,便豪爽地一挥手,说都拿去,看完再来还。我如获至宝,欣欣然搬回了家。
夜晚,写完作业后,我开始啃读这些书,读累了会不由得望向窗外,星空浩瀚,星子们似在窃窃私语,用闪烁的莫尔斯电码传递着亘古的秘密,也用细细碎碎的光亮不断打量我。那些夜晚,我与奥利弗·退斯特一起在伦敦街头流浪,与卡西莫多一起在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守望,与冉阿让一起在巴黎的下水道中逃亡……就像做了一个又一个的梦。
再后来,我加入了贝塔斯曼书友会,购书成了一种习惯,那些书籍以邮寄的方式穿越千山万水,来到了小岛,成为一名少女的精神财富。我的小书架逐渐丰盈起来,像一块微型的陆地,承载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。那些书籍陪伴我,滋养我,让我看到了小岛之外广阔而神奇的天地,也培养了我初期的文学感观。
2
小学和初中我都得遇很好的语文老师,她们在我的作文本上写下鼓励人心的评语,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朗读或贴在班级的墙上,初中语文老师甚至建议:你以后可以尝试走写作这条路。当然,彼时的我并未在意,作家,那也太不现实了,还是先把考试考好吧。
小岛靠海吃海,岛上的男人多为海员和渔民,女人们则在家里照顾孩子和老人,闲余时间串串门、聊聊天、搓搓麻将,直至终老。这种一眼能望到头的生活让年少的我感到一丝不安,我害怕重复这样的人生,隐约的抗拒和不甘心不知该找谁诉说,不知该去哪里找寻答案。一个小女孩在成长过程中积攒了越来越多的心事,总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,我开始写日记,写下迷惘,写下思考,写下模糊的愿望,写下转瞬即逝的坚定,写下时有时无的信心。当表达的欲望达到顶点,遂忍不住在草稿本上写了一篇小文,标题借用了一首歌的名字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。随后,买来方格稿纸,用钢笔一字一句地誊写,待墨迹晾干,将稿纸横着对折,再竖着对折,装进早已填好地址的信封,贴上邮票。我捧起信封,心口微微发热,我知道,它会长出翅膀,载着希冀飞向远方。
那是我第一次投稿,投给《舟山少年报》,初中时,每个班级都订了这份报纸。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起投稿之事,忐忑与期待像两个调皮的小孩,在我的心里追逐打闹,每次,班长去领报纸,我的心就狂跳,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。
惊喜来得毫无征兆,隔壁班一个同学先看到了报纸,然后到我们教室嚷嚷开了。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占了报纸很小的一个角落,真正的豆腐块,油墨香那么好闻,我的鼻子凑近报纸,猛吸了好几口。那张报纸被我极其郑重地藏进了床头柜的抽屉里,时不时,我会打开抽屉看看,仿佛它是一颗正在发芽的种子,会长出藤蔓,开出花朵。接着,收到了汇款单,七块钱的稿费,我全然忘记用这笔钱买了什么,却时常想起那张浅绿色的稿费单,油墨数字扁扁地趴于其上,如明亮的光斑,那么闪耀。
时光是弹弓上的楝果,嗖一下就飞出去老远,生活这列永不停站的列车,轰隆隆载着我一路向前。在成人世界的摸爬滚打和日复一日的庸常、忙乱间,偶尔,我也会阅读,会望望星空,想想在星空下做过的梦。
3
我真正进行文学创作,是在离开了小岛后。与其说遇到了某个契机,不如理解为水到渠成,那种冥冥之中的引领,从我孩童时代就开始了。一直认为,文学之路从来不是刻意选择的结果,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长,是一场心甘情愿的精神迁徙。
数字时代,文学似乎成了一种奢侈的慢艺术。写作是一条孤独的路,没有惊涛骇浪,没有蜃楼幻境,只有日复一日的潮起潮落。我沉浸于这样看似枯燥的重复,在电脑键盘上敲下一个又一个字,一篇又一篇文章,作品发表在各级刊物上,书一本接一本地出版。我对写作饱含热情,有时候,颇有一种写得停不下来的势头,就像海岛上的野花,一旦碰触到一点点土壤,就努力生根,兀自盛开。
写作也是艰苦卓绝的自我搏斗。打磨、修改、推敲、取舍、推倒重来……像深海潜泳,需要克服多种压力才能触及被日常掩埋的珍珠。近几年,我着手创作海岛和海洋系列,与此有关的一切,我都特别想挖掘和呈现。当我在文字里回望故乡的小岛,发现那里的每一块礁石都藏着故事,每一朵浪花都唱着歌谣,每一天的潮汐都跳动着深沉的生命韵律。我写海洋的幽昧和丰富,写海岛生活的野朴和神秘,写渐行渐远的传统习俗,写海上讨生活的艰辛,写鱼汛来时港口的喧嚣,写台风过境后的遍地狼藉、写小岛在时代里的变迁……这些文字带着咸腥的真实与生命的粗粝,地理范围的框定并无妨碍它在某种意义上获得辽阔。我不只为记录,也是在告别。
文学是我一直仰望的星空,这份仰望大概源于在夏夜里听奶奶讲故事之时,而写作者就是星空下的造梦者,在人间用文字收集星光。
 分享
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