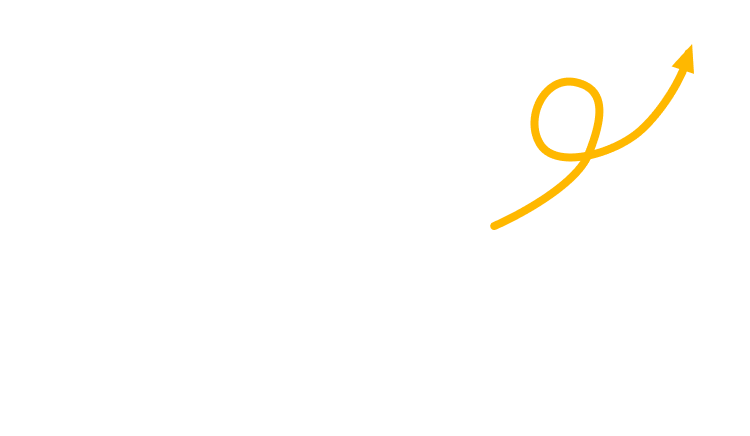那段时间,回到离开40年的小村庄看看的念头一直在我心中萌动。终于,在一个夏日,我放下手头的一堆杂事,背上简单的行囊,踏上了归程。
再回到儿时的村庄,我没想过究竟要寻找什么,也没想过想见谁,甚至说不清回去的真正目的,只感觉内心深处有一声热切的召唤。我无法抗拒,就像当年远方迷人的诱惑,让我义无反顾地离开村庄。
先乘飞机,然后转火车,再乘公交车,最后是步行。终于踏上那条铺了沙石的村路,我的心中并没有近乡情更怯的感觉,反倒有些轻松。加宽的村路上没了昔日的尘土飞扬,路边一丛丛扫帚梅开得正艳;散落的蒲公英在肆意地嫩绿;被切割成一块块的庄稼地里,大豆枝高荚满,白菜饱满健硕,萝卜长缨招摇……眼前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,让我感觉时光似乎并没有走远,让我看到好多年前的一些影子。
越来越近,一排排砖瓦房出现在眼前。村庄的变化很醒目,连名字都更改了。村边,我熟悉的小学操场已变成一家木制品加工厂的仓房,那一溜土坯房教室被翻盖成三层楼房。不等走近,就听到了机器的轰鸣声。
听说,秋生现在是这家工厂的老板,村里不少人都在给他打工。我记得,当年我离开村庄时,秋生刚刚三岁,长得又矮又瘦,还爱哭鼻子,整天跟在他哥哥春生的屁股后面,像个甩不掉的尾巴。
村庄的西头,我住过的那两间土坯房已不见了,房前的两棵老榆树也不见了,房西那块承载了我无数童年往事的草甸子更是消失得干干净净。那块绿了黄、黄了又绿的草甸子,藏在草丛里的鸟鸣,村民们踩出来的一条条蜿蜒的小径,连同穿过草甸子的那条无名小河……都被一大排蔬菜塑料大棚替换了。我记忆底片上的那些鲜亮的景物,都已无影无踪了。像一个突然的闯入者,我一脸错愕地站在那里,暗自叩问:这就是我心心念念的村庄吗?
没过多久,我就释然了:时光只那么轻轻地一晃,就将我晃得两鬓斑驳了。如此,我魂牵梦萦的村庄模样变化大一些,又何必惊讶呢?
我见到了儿时的玩伴旺财,旺财并没有发财,好在身体不错,一个人照料着三十多亩地,靠雇别人的机器播种和收割,倒也温饱不愁。旺财比较看得开:草木一样普通的庄稼人,过上这样的日子他很知足了。
秋生对我的归来十分热情,他指挥着家人杀鸡宰羊,弄了一大桌子极丰盛的菜,拿出了珍藏多年的茅台酒。酒杯举起来,秋生大着嗓门:“欢迎不远千里归来的崔教授,感谢你为家乡争得了骄傲,也感谢你始终不忘家乡的井水。家人相聚,我们要畅快地连干三杯!”酒至酣时,秋生突然落泪:“我哥那年外出打工,为着省十几块钱的车费,坐了严重超载的黑车,在离家十里路的小桥上,车翻了,人没了,媳妇还没过门呢。”
我听说过那次车祸,但不知道遇难者里面就有我儿时要好的玩伴春生,还有一笑起来脸上就露出两个酒窝的小学同学立新。
“从前的日子苦,家家都不容易啊。”伤感袭上心头,我不知该如何安慰秋生。
“现在生活好了,就是常常忍不住怀旧。”秋生擦擦眼泪,继续张罗着喝酒。
“爱怀旧,那是因为老了。”一个衣着光鲜的中年女子推门而入,一点儿也不见外地坐到酒桌上。秋生忙给我介绍,说她是我家后院老郑家的三姑娘丽珠,小名丫蛋。
我大脑急速地转了半天,也没从记忆里打捞出丽珠的影子,只得坦言:“看我这破脑子,怎么忘了你小时候的俊模样呢。”丽珠没怪罪我,还帮我打圆场:“你是省城大学教授,接触到的人天南海北、成千上万,哪能记得我呢?再说了,我小时候长得猫三狗四的,记不起来了更好。”丽珠又抖出我少年时的两件窘事:一是一年夏天,我到小河里摸鱼,短裤被小伙伴藏了起来,我在河里泡了大半天,才等到父亲送来衣服;二是一年冬天,我下菜窖里取冬菜,结果被二氧化碳熏倒了,差一点儿酿成悲剧。
接下来,我们不停地打开一个又一个话题,聊起一个个人、一件件事,过往与现在,不断地穿插起来。于是,我得知当年村庄里有名的“庄稼把式”陈德心举家去山东了,成了远近闻名的种菜大户;朱铁匠当年的身体多棒啊,偏偏跟他的父亲一样患了肝癌,十年前就去世了;村小学刘校长的大儿子当上了副县长;这些年来,村庄里有几十个孩子考上了大学,但没有一个回来的。现在的村庄里,年轻人越来越少了,种地的多是上了年纪的人,不少房子都空着,偶尔有城里人想休闲了,就过来住几天,感受一下乡村的平静生活……
秋生问我:“这次回来是不是想找寻一下记忆里的村庄?”我摇摇头:“早就知道找不回来了,我依然还要回来,是因为心中始终难以割舍的念想。”
“念想,这个词好,人活着就离不开念想。人有了念想,心里就不空落了,”秋生理解我的乡土情结,“无论走到哪里,走了多久,心中最念想的,还是你出发的地方,对吗?”
是的,明明知道藏在心中的那个村庄早已物非人非,再也回不去了,我仍怀揣着强烈的念想,一路风尘仆仆地赶来,带着些许的欢喜,也带着些许的伤感。就像天空中慢慢赶路的那朵白云,它不知道自己将在哪里驻足,在哪里安息,奔波是今生的宿命,或许它偶尔也会想起村庄里的那间茅草屋,想起那根矮矮的烟囱。
只是,回不去的村庄一直在我心头,那么诗意,那么人间烟火。
 分享
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