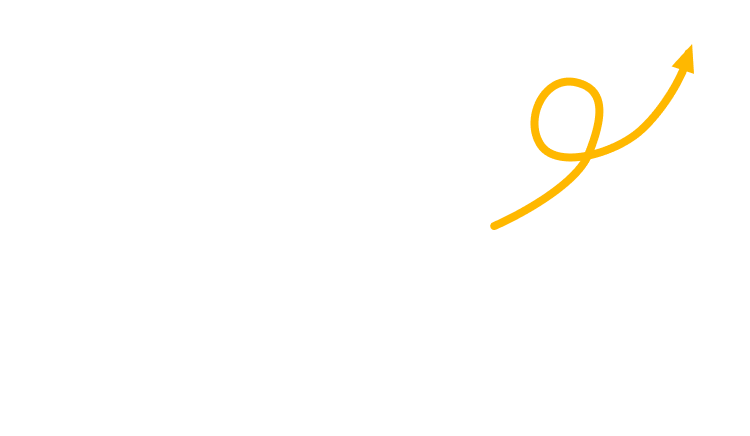雨来了,猫着步子,攀着浅浅的灯光,起初是三两滴试探性地小叩着窗棂,仿佛伶人试音的琵琶弦,而后便淅淅沥沥地倾泻下来。我正独坐于窗前,案头摊着一卷泛黄的《元曲选》,那些蜷缩在纸页间的句子,被潮湿的空气浸润,渐渐舒展开伶仃的腰肢欣欣然鲜活起来。
关汉卿的《大德歌》卧在平平仄仄的雨声里。“风飘飘,雨潇潇,便做陈抟睡不着。”七百年前的雨与今日的雨竟在窗棂上不期而遇,将失眠者的辗转婉约成连绵的平仄。书页间的墨字被水汽洇开,恍惚有皂隶的梆子声穿透雨幕,应和着大都城里更夫的铜锣。元人的雨是掺着驼铃声的,沿着丝绸之路的毛细血管,将西域的沙粒一颗一颗地洒落在勾栏瓦舍的琉璃檐上。
突然,马致远的《秋思》被一阵疾风掀动。“枯藤老树昏鸦”六个字从纸面倏地飘起来,在雨雾中结成黑色的冰。我想象这位“万花丛里马神仙”如何用枯笔蘸着涿州的黄土,在宣纸上皴擦出整个时代的荒寒。此刻,窗外确有老槐树在雨中瑟缩,但昏鸦早已遁入博物馆的标本架,唯有空调外机在重复单调的鸦啼。
雨下得更密了。白朴的《梧桐雨》开始吟唱,唐明皇的眼泪与今天的雨水在时空的褶皱里拥抱。那些“润蒙蒙杨柳雨”“细丝丝梅子雨”,此刻正真真切切地浇灌着二十一世纪的混凝土森林。
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在潮湿中绽放出奇异的光泽。当“碧云天,黄花地”的唱词漫过电子阅读器的荧光屏,我分明看见大观园里的黛玉在偷听墙外的昆腔。元曲的基因潜伏在《红楼梦》的骨髓里,此刻又被雨水冲刷出来,化作阳台绿萝上新生的气根。
雨声忽然转成了仄调。郑光祖的《倩女离魂》从书页间飘出,那些“魂逐东风吹不去”的句子缠绕着雨丝,当代的倩女们在雨丝中踩着共享单车穿过斑马线。我触摸着纸页上凸起的铅字,像抚摸戏曲博物馆里褪色的戏服,金线仍亮,但再无人能穿上它翩翩起舞。
窗外的雨幕忽然映出虹霓。张养浩的《山坡羊》顺着七彩的光爬上来,“峰峦如聚,波涛如怒”的咏叹撞在玻璃幕墙上,碎成无数个外卖小哥的黄色雨衣。潼关路已成高速公路服务区,但元曲里的黄河水依然在流。
书页上的《天净沙》突然完成了它的电子迁徙——枯藤变成了电缆塔,老树化作信号基站,而昏鸦正以无人机的形态盘旋。马神仙若见此景,或许会把“断肠人在天涯”改写为“二维码飘在云端”。元曲的遗传密码,终究在数字时代的雨水中完成了转录。
合上书时,忽然发现封底的定价标签正在脱落。那些曾经价值“至元通行宝钞贰贯”的曲文,如今在旧书网上标价“五元五角”包邮。雨停了,但元曲的韵律仍在混凝土缝隙里生长,像极了被车轮碾过又复生的地锦草,用五百年攀缘的执着,在钢化玻璃的悬崖上写着新的散套。
 分享
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