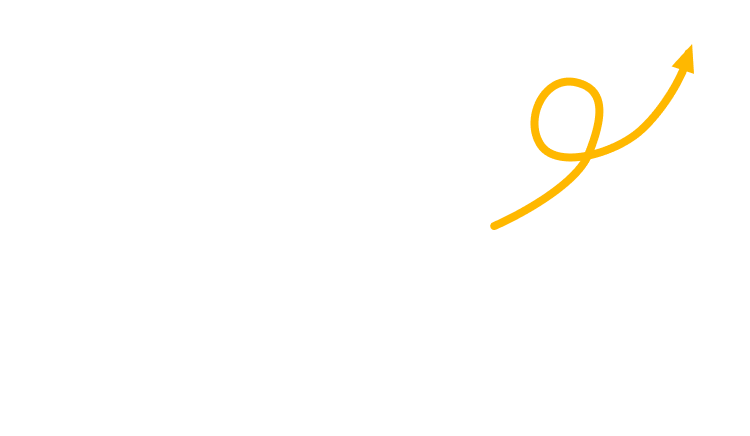过梁马
马在辽西扮演的是忍辱负重的角色。虽长得英俊高大,能日行千里,鬃毛亮丽,步伐矫捷,马儿依然只能驾辕拉车、上集赶店,屈辱于马夫之手,胼死于槽枥之间。
这次龙潭大峡谷一行,我们除了坐船,也坐了马车——从山腰上到山顶,再从山顶下到山脚。这段距离不长,只是车夫将马车装饰得五彩华丽:车上是多彩的帐篷,马脖子上摇晃着悦耳的铃铛,就连马屁股上也盖上了红色的屁帘,以免有碍观瞻。再加上六月末的烈阳,晒得水泥路面上直冒白火,让你由不得想赖在马车上游荡山间,观山望景,走马观花,也算是对车夫周到服务的一种成全。
我们坐上了一辆由一匹枣红马扛驾的马车,一路上迎风唠嗑,喜笑颜开。红色帐篷轻摇着下摆送来徐徐微风,马慢悠悠地走,车颤巍巍地行进,车夫间或甩响空中的鞭子,叫嚣眼前的牲口加快脚步。马车爬上高坡时,我们看见身边有空着的马车三三两两地从底下上来,马呼噜呼噜地喘,它们忍受了四十度高温的暴晒,也忍得主人编着花儿的教唆和训斥……梁越来越陡,天越来越热,我们这匹马的喘息声突然越来越粗,越来越急促起来了,雾一样的热气从它粗大的鼻孔排出来,飘散在干燥的空气中形成霜一样的回流。它的步伐越来越慢,越来越乱,越来越前步不搭后蹄。我忍不住从马车右前座跳了下来随车步行,另一位老哥也这样做了,他边走边说:“天这么热,这马太可怜了,你瞧它累得呼哧带喘……”车老板不以为意,建议我们马上上去,好像不上去就对不起我们给他的五元钱似的。他说他的牲口挺得住,呼喘是正常的。
下坡了,马儿的步子明显轻快了许多,它的头昂得老高,和山下的松树平行;它的尾翘得老俏,掀动火红的屁帘。马高兴,我们也跟着高兴,绿树红花,山风浩荡,爱物及人,心事渺茫……
下车时,正好路过车夫的家,他一边接过游客们递过的一张一张五元钞票,一边说,一会儿要回家饮一饮辛苦的老马,它受不住了,要加一加油,补充些能量。我们下山,无心回望山间的老马。它们在朝晖夕阴中,在峰林与树林间交卸着一天的工事,没有怨言,只想饥渴时饱喝一顿,黑夜时望一眼露珠和黎明……
摆渡女
龙潭大峡谷,两岸青山相对出,几爿孤舟谷边来。装载着柴油发动机的小艇带着我们穿行过几座孤峰,抛锚上岸以后,导游说,下一站依然是坐船,只不过坐的是人划的船,而不是机动的船。
船老大终于把船划过来了,她们一位五六十岁,一位三四十岁,是一对婆媳。她们划的船不是小说《边城》里翠翠祖孙俩划的轻快的木船,而是看上去庞大又坚固,用钢铁铸成的小型游船。她们一会儿拽着湖心的航标绳,一会儿又用有力的手掌舞动双桨,加快游船的行速,控制船只的平衡。老大娘皮肤黝黑,头发更黑,那沉淀到毛孔里的黑色是被太阳炙烤过的坚毅和犀利。老大娘说,这几年龙潭大峡谷火了,即便是淡季,游客也不少,靠着丰富的行船经验,她们的生意即便在雨天,也是“船”庭若市。
她们是老船把式了,驶过的湖面风平浪静,驶离的位置恰到好处,把最多的景点和最好的角度留给游客。弯腰时的杭育、抬头时的喘息……无数的摆渡女们除了用山歌表情达愿,更靠内心的坚韧憧憬着终点。
野渡无人舟不横,因为没有春潮带雨,没有晚来湍急。摆渡女洗尽铅华,她们还是本色的使者,捎来自然的芬芳,惊起岸边的飞沙与空中的白鹭……
工棚
闲来无事,骑自行车瞎逛,路遇搭建在玉米地旁边的几个工棚。工棚是用帆布做的,属临时性质。这处工地的活儿干完了,帆布收起,继续南北西东的“转战”。帆布搭的工棚大小不一,有几人一间的,也有十几人几十人一间的。这两年我所看到的多是小工棚,也就一间砖房大小,里面住三五个工人。工棚就是个存宿的地方,即便大敞着口、没有门,住着也是燥热无比的。工棚多搭在庄稼地边,蚊子多是一定的,蚂蚱会跳上棚顶,蛐蛐在夜里伴奏,半夜说不定还会有蛇温柔地爬进来。
向晚的微风习习吹过时,我看见几位工人弓着腰坐在棚口的塑料椅子上,抽着烟,聊着天。这是几位老工人,穿着被汗渍得发黄的白背心,烟圈在玉米芒前荡漾开去。玩笑开得肆意时,他们的笑声就突然高亢爽朗起来,他们觉得出来干活是件很痛快的事情,老婆孩子管不着,老婆孩子在家他们也放心,他们只管使足力气,赚钱供养一大家子。
年轻的工人光着膀子,几个一群地先到小吃摊上喝酒划拳吃炸串,然后肩并肩地走在油路上、土路上,吼着歌,嚷着口哨,风风火火而过。小伙子们个子高高的,身形瘦瘦的,脊背黑得粗糙,上面落满了土,骨头突兀得向外一纵一纵地支棱着。
工棚附近就是正在拔高的大楼。大楼的四周也是庄稼地,庄稼地前方是绵延的小山,后方是奔腾的河流。钢筋水泥给山和水带来了硬度与笔挺,庄稼地里的高楼葳蕤、雄壮,有水位,有风声,有气脉。
还有一种露天的工棚。说它露天,是因为一块纱布被四根木杆使劲撑着,只有顶,没有壁。木杆上拴着一盏电灯,闪着白亮的光,一群蠓虫围着它不知疲倦地旋转。有个当地模样的人抱来一团荆梢,点着它驱散蚊子,民间称之为笼蚊子——把蚊子笼罩住,呛死在火光之中,大抵如此解释吧。我的车轮没有停下,我想起童年时在房顶睡觉的情景,避暑纳凉,远蝇蚊,不胜美哉!
还有砖筑的工棚。老家的砖厂旁就有,是老板给来自敖汉旗的工人们盖的。二十米一长溜,里面都是砂泥墙,灰咕隆咚,光线昏暗。窗户没钉玻璃,钉的是塑料,刮大风,下冰雹,塑料被刮开了,出了洞。工棚坐落在小山脚下,工人们收工后吃完大锅饭菜,不是上山采莲,而是汇聚到营子中的广场上扭秧歌、瞄人影儿、看热闹。敖汉旗的工人很能干,也很守纪,他们的工棚开放着,裸露着,却鲜有事故传出。工人们多数是男的,白天在窑里烧砖拉着小车运砖,女工们给他们打下手。女工们的脖子上搭着汗巾,瞅着他们的毛愣和憨厚,笑得他们吐气扬眉,把车把抬得很高很高。
几年以后,砖砌的工棚荒废了,里面土炕坍塌,棚顶蛛网暗结。砖厂夷为平地,变为养殖场。砖厂山后的布搭工棚渐渐多了起来,伴随着机械的嘶鸣、大地的皴裂、烈日下的劳动号子以及安全帽檐下轻淌的汗珠、嘴角飞扬的热血沸腾……
 分享
分享